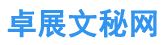[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有些学者主张道德标准,但是道德标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地位是无法与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与团结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相提并论的。《春秋》史观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且蕴涵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乃至一种信仰,并已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民族精神。正因于此,中国史学的道德标准具有了特殊功能,如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具有追罚和补偿功能;维护社会与历史公正等。
[关键词]历史人物;评价;道德标准
[作者简介]高希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2—0030—05
“青史凭谁定是非?”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也最富挑战性的内容之一,它吸引着也困扰着众多学者。中国传统史学聚焦于具体人物的褒贬臧否,对抽象的评价标准问题注意不多。近现代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注重理论层面的探索,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的主导范式,因而唯物史观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绳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毕竟是一个多面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诠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方面自然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于是各家观点争奇斗艳,构成史学界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建国以来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这一阶段,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尺度,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讨论是在唯物史观一元论标准的框架内进行的,尽管内部存在很大分歧和差异。在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标准是两个并行的标准,即历史作用标准和阶级标准,阶级标准一度独自占主导优势。这主要表现为,即使所谓剥削阶级的人物推动了所谓的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统一,也要非得给他加上一个“阶级”性的局限不可。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是后一阶段,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讨论开始跳脱历史作用标准和阶级标准模式。在这一阶段,阶级标准日渐式微。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标准。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也逐渐突破历史作用评价标准的一元主导模式,而日益走向多元化,但全新的标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建国后有些学者主张坚持道德标准,但是道德标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地位是无法与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与团结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相提并论的。受政治与社会语境等因素的限制,道德标准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20世纪50~60年代在历史人物的讨论中,涉及道德标准问题。嵇文甫主张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三个标准: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对第三条标准,他解释说,历史上有些人没有具体的创作发明,而要说他代表进步方面,也说不上,比如董狐、苏武等人就是如此,但是他们表现了中国人的高贵品质,立了德,对我们民族也有利,所以也应该予以肯定。吴晗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与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其私生活出发,也就是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他认为,个人生活作风虽然对历史有一定影响,但这是次要方面,不是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王昆仑认为,尽管中华民族有自己从来的道德观点,不可忽视,可是对历史人物估价还是首先衡量他对历史的客观效果。吴泽、谢天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主要以其政治实践为依据,但并不排斥对人物品质和个性的估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的文著涉及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道德评价问题。李时岳、赵矢元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要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同时他们还认为,坚持历史作用为根本标准,一定要反对以人的主观因素、道德规范为主要标准。吴廷嘉认为,个人品质不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乃至唯一标准。“作为历史人物总体评价的主要标准,应以其社会活动和实践后果为正宗和大宗”,但不抹杀道德评价的意义。苏双碧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气节是必须考察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他同时提出四点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把反对改革、反对西方说成是爱国爱民的气节;其二,在运用气节观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具体分析;其三,对旧王朝的死硬派不应多加肯定;其四,不应肯定封建的节烈观。罗耀九认为,“气节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项标准”,“爱国主义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政治标准”。江连山把是否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标准作为评价标准之一。王学典认为道德标准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可缺少的标准,并在当代具有重大意义。
建国后,史学研究及历史人物研究的这种状况与毛泽东及其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从1949年开始,与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文化领域一样,我们的史坛也真正进入了一个毛泽东时代。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历史学界的轴心,宣传、阐释、学习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定着、覆盖着中国的史学界”。毛泽东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段论述,是毛泽东全部历史理论的基石,是贯穿始终的红线。以历史作用标准和阶级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标准是一种政治标准,它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相关观点为立论的前提、论据或结论,在理论探讨的深度上没有超出他们,最多只是细枝末节的修补或诠释。这种标准强调了历史与社会发展的物质方面,而忽略了精神与道德方面。或者说这种标准主要强调了事功判断而忽略了价值道德判断。在这个所谓“民族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规律”面前,人类无法对其行为负责,各种暴行及恶政也就有了借口,个体生命乃至部分群体的生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必然规律”的现实执行人,无论有多么大的道德问题,似乎也必须肯定乃至歌颂。“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就这样可以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人们甚至认为,只有摆脱了伦理的束缚,才能更好地执行“历史的规律”,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道德因此而荡然无存,道德伦理尺度也因此丧失了立足之地。建国后,人们为曹操公然翻案,做几千年来人们不敢做的为“恶”辩护,其
深层的原因就在这里。
道德标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或者说在历史人物评价中道德该不该是一种主要的评价标准呢?坚持道德标准,不但与社会建构的性质与内容有关,也与中国史学的特殊性及其特殊功能有很大的关系。社会发展并非仅仅以经济增长为准,仅仅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为指标,并非完全指向物质;而应以社会与人的综合发展为宗旨。社会进步也并非仅仅是物质的进步,而是社会与人等整体综合的进步。人除了物质需要,还有精神、价值需要。社会除了物质、经济,还有精神、文化。而建国后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无疑鼓励了重物轻人的片面发展观,鼓励了重成功轻道德价值的历史观,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颂扬了“恶”,而放弃了中国史学所特有的警示、训诫、育化人心和维护社会与历史公正的功能。中国史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于《春秋》史观。所谓《春秋》史观,一日记录史实,讲求信而有征;二日倡言人伦价值,褒贬善恶,意在“彰显”人物不朽于青史之中。这种历史观发轫于孔夫子的《春秋》,光大于司马迁的《史记》。《春秋》史观所主张的善恶褒贬,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也并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是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乃至一种信仰:“坚信行善者即使生前有德而无福,多经苦难,也一定会获善报,会获历史褒扬;坚信作恶者即使生前无德而有福,多享富贵,也一定会遭恶报,会遭历史唾骂。”并且,前者很有可能因德及子孙而为他们永久祭祀,如岳飞香火八百年长明不息;后者则很有可能因殃及子孙而为他们永久抛弃,如秦桧成了人神共逐的孤魂野鬼。《春秋》史观所倡导的这种道德标准及其所蕴涵的“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成了此后许许多多中国历史学家所遵奉的著史理念,两千年无异辞,并已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民族精神。几乎所有文明的核心价值,都至少包含“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至于如何阐释这些理念,不同的文明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基督教文明采取宣讲《圣经》的方式,伊斯兰教文明采取宣讲《古兰经》的方式,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明,则主要采取刻诸青史的方式。以《春秋》史观为代表的中国史学才具有了某种类似宗教的功能。中国史学具双重职能:一是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二是维系人伦价值,讲求道德褒贬。前一职能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具有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有的职能,它担载着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承载着类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承载的东西。中国史学与宗教虽在记述内容上不同,前者记史,后者敬神,但在都在维系人伦价值这一点上却功能相近。正是由于中国史学的这种特殊功能及其所塑造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宗教功能的历史意识,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体现《春秋》史观的历史,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没有全国性宗教的民族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并具有以下功能。
其一,历史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感淡薄的民族里,能够让人们,特别是那些权倾天下的强势人物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只有史书了。中国史书既注重如实直书又注重善恶褒贬,这就在现实中对人们特别是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秦始皇、曹操、武则天之所以在古代社会成为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主要由于中国史学所特有的功能。这就把人们特别是权势人物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道德范围之内。当然对那些没有廉耻感的人来说,这当然无异于对牛弹琴。在中国两千年来,承载这种特殊功能的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的监护人。一旦脱离这个监护人,这个被监护人就可能由养子变成居无定所行无定规的浪子,乃至无法无天者。如古代和近现代中国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势人物们,古有秦始皇,近有慈禧太后等等。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起于乱世的草莽英雄和少数不知廉耻的浑球外,大多数精英人物或政治权势人物都曾把读史作为自己的一门必修功课,都很注意自己的道德修行。熟读史书,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读史书,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书的份量。史书既是他们从事政务的教科书,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鉴定书,故受其震慑。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思想家、政治家或其他人物,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而不愿意在历史中留下骂名,并蒙羞于子孙。比如仍为祖宗蒙羞而抬不起头来的秦桧子孙。自称是秦桧第三十二世孙的秦良称:“我从来不向陌生人提到我是秦氏后人。”中国人总喜欢在自己的身后留下点什么。这留下的东西除了血脉外,就数功业和名声为重了,而名声则尤为重要,即使事功泛泛的人也想留下美名于人间,更何况功业卓著权势显赫者呢。但是许多权势家族,由于社会地位很高而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往往能做寻常百姓所不能做甚至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事。其中一些人往往姿情纵欲、无所顾及、内窃国库、外敛民财、裙带骄横、衙内放纵,而最终或败于家业挥霍,或败于民众口碑。当然这种祸国殃民的丑类丑事,也就成了当代特别是后世史家口诛笔伐的题材了。
其二,历史具有追罚和补偿功能,起到维护社会与历史公正的作用。这种功能使现世中的人们特别是权势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是要在历史中盖棺定论的。也就是说,权势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赢得现世未必赢得历史;失败于现世,未必失败于历史。即让那些生前有福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而“遗臭万年”,如古之秦桧;让那些生前有德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而“流芳百世”,如古之岳飞。在现世中的成功者未必是历史中的成功者,比如慈禧太后在历史中永遭骂名。现世的所谓成功者,在现世角逐中可能做到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制造人间灾难,但是他们在历史中却遭到子孙后代的谩骂与唾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老佛爷慈禧和秦桧已被死死地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典型的例证。在现世中的失败者未必是在历史中的失败者,而是历史中的成功者而享有盛名与不朽,比如今之瞿秋白。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因为在历史中现实统治权受历史话语权的制约;政治人物的行为是要延续到历史中的,他们的胜负是由历史说了算的。所以说“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样类似的观点有极大的片面性。“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难摆平却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做恶事;一个有德的人未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屡经苦难。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在这德与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对那些有福无德的人予以追罚,对那些有德无福的人予以补偿。各民族如何实现这种
追罚和补偿,没有统一途径。“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途径来实现的,即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下地狱’,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上天堂’。”我们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著史途径来实现的,这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瞑”这句名言里得到经典表述。因此,历史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起到维护公正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常常是通过褒贬对象的生前与身后的时间差来实现的。
其三,历史把我们民族塑造成一个善于记忆的民族。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地喜欢记史,喜欢把发生在身边的、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以遗后人,或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或作为他们立身处世的龟鉴。人们记史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方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国史;在民间社会有地方志、野史、家谱、家史、墓志、说唱、口耳相传史等等。总之,总有人以不同的形式把那些或有德有义的贤良,或无德无义的小丑,记录下来,使他们或是享有盛名而流芳百世,或是遭后人唾骂而遗臭万年。私家修史可为中国人喜欢记史的例证。私家修史在中国历史上巍巍壮观。这样的史家,先秦以孔子为代表。自汉迄清,代有其人,如荀悦、袁宏、裴松之、范哗、萧子显、李百药、杜佑、郑樵、胡三省,马端临、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全祖望、章学诚、崔述等等。有些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通》《资治通鉴》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私家修史,特别是那些文章道德皆佳的史家修史本身就是积极用历史干预社会进程的士人风范。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
其四,历史使得那些在现世中绝望的人们怀有最后的希望,即希望历史能作出公正评价,还他们以清白。中国人所敬畏的历史与宗教徒所敬畏的真主或上帝等,有某些共同点,即都具有公正品格和终极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作出各得其所的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于是历史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读书人在其一生,特别是人生紧要关头所倚重的精神支柱。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即能超越人的生死大限的信念,为古代中国一些“士”所坚守,如文天祥诗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最经典的例证。历史无疑是文天祥等坦然献出生命的希望,是这些殉难者最后的希望,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可以说,就是这个希望支撑着他们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走过了常人无法走过的路。
总上所述,道德标准在中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在道德滑坡、精神萎靡的小品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在史学研究与著述中坚持和发扬这种道德传统,在古代,道德褒贬重在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强调等级秩序。这种做法在今天已不合时宜,但其中所蕴涵的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当今,有必要根据新时代的具体实际对古代道德标准进行转换,以确立新的道德标准。新的道德标准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最基本的价值伦理;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正义与公正。从而新的道德标准也就有了三个基本功能:一是肯定、维护和普及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二是谴责丑恶、暴行等消极的东西;三是维护正义和公正。尤其是,不应该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以所谓的“进步”为根据来粉饰、赞美、肯定暴行和屠戮等消极、负面的东西。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研究的不是冷冰冰的物质世界,而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作为精神存在的人不可能不与道德价值发生关联,历史学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尽管史学家时常面对事功判断与道德价值判断的紧张,但在维护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犹豫。以《春秋》史观为核心的中国史学,对维护历史与社会正义,对塑造和育化人心,对维护中国的优良传统起了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尽管其中蕴涵的道德标准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正是这种人心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性格气质,特别是士人风骨。而这种士人风骨在某种意义上又恰恰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春秋》史观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且其中蕴涵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这种理念和信念并已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民族精神。也就是说,道德标准的意义并不仅仅在道德标准本身,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捍卫,对基本价值准则、历史与社会公正的维护。它维护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东西。若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必须重建中国的著史理念,复兴中国的史学传统。这就是道德标准于当今史学和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周志华]